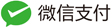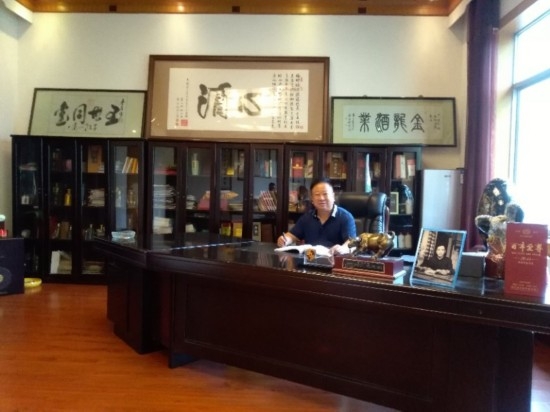新华在线网 祁成志
艺术简介

张慧旭,1978年生,江苏射阳人,师从张锡庚先生。硕士,高级工程师。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苏州相城区书协理事。《书法报》曾作专版介绍。
作品入展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展、第八届中国书坛新人新作展、“新歌墨韵颂中华”年江苏当代名家书法邀请展、第四届林散之奖书法双年展、第二届“江苏书法奖”、得意之作——苏州市中青年书法篆刻精英提名展等重大展览20余次。作品获书法报“第三届全国教师现场书画创评”特等奖、“翰墨薪传”全国中小学师生书法比赛教师组三等奖、第十届“观音山杯”全国书法艺术大展优秀奖、第二届“象山书院杯”全国书法大赛优秀奖、首届“文笔光华杯”全国书法艺术大展“文心奖”、苏州第一、二届“繁星奖”银奖等重要奖项10余次。


















《“草”书于前》
慧旭来电,说正与同城书友张罗着、忙乎着,准备搞一次书法作品联展。闻此消息,作为舅舅的我,心中自是喜欢的紧:凭着建筑工程专业技术养家糊口的外甥,业之余有此雅好,居然还整出点名堂,真是让我开心,可以喝杯小酒了。不过,紧接着他 “一口价”提出要我为之写序,让我有点犯难——俺老孙识字,但不是书家,更不谙书艺;俺老孙也曾多次尾随名家出入于书画厅堂,但只是沾点墨香、装装斯文的看客一枚。拙于“书”,怯于“法”,不入其门如我者,又如何做这序耶? 宛如他幼时在我面前好话讨饶,那天外甥一番甜言蜜语随即让我“俯首甘为”了。于是,我也找出诸多理由为自己壮胆:我是看着慧旭长大的——追随我的脚步,出生于乡村的他,也是一番苦读,凭藉胸中点墨考入大学,然后以拳拳之心、一技之能耐,立足于业界,然而他用情于笔墨,专注于书艺,则是因童蒙开启,日积而月累,孜孜不辍,渐渐有今日之“气象”——知外甥者莫若舅舅啊。
我与慧旭的故乡在苏北射阳一个叫“红星大队”的地方,那是苏北平原的深处,距离黄海和丹顶鹤自然保护区大约六七十公里。我们都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少年时光,从初中、高中、大学,再到工作,我与他也都是越走离家越远,如今落脚谋生于江南两座比邻的城市——苏州、无锡。只是故乡那个巴掌大的地方,一直装在我们心中。春夏秋冬——田野、河流、庄稼、鸟鸣虫声、茫茫星空、风霜雨雪,过去曾经是、如今依然是我们的养料。如果你一定要我像旅游手册一样用一句话描述那块地方,那我只能借用孙昕晨多次说过的那句话回答你:我知道其中的亲切。
我为什么要说到故土?因为任何一个人、一件事的源头,都是一滴奇妙之水,何况书法啊。张慧旭那最初的一滴墨水啊,如今你在哪里? 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的中国农村,标志性的符号是茅屋、农具和粗布衣裳。慧旭的妈妈——我的姐姐,只读了两年书;我姐夫——慧旭他爸是位小学教师,在我眼中,他真正的强项不是教学,而是打牌,一旦上了牌桌,他本来就炯炯有神的眼睛,滴溜溜转得更凶了,稍不留心,他就瞅到了你手里的牌。而且,嘴里念念有词,仿佛是某种咒语,搞得你心神不宁,然后他再从你的表情里窥见你内心的活动。当然,在学校里,会打牌不算什么优点,慧旭他爸真正被人尊敬的是每到年根岁底为乡亲们写春联。在乡下,毛笔字写得好,每逢红白喜事,都会有人上门求你。三四十年前在农村,一手好的毛笔字,是很有文化的象征。慧旭他爸的毛笔字不是什么书法,他是“原生态”那一路——用钢笔字的写法换了毛笔写罢了。不过,也许看过一两本颜真卿、柳公权,然后琢磨一下点横竖撇,再然后就开始自说自“画”,反正周边农民永远是一片啧啧赞扬之声。他也像庖丁解牛一样,提笔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然后任意挥洒。
自幼围在书桌边看父亲为乡亲们展纸磨墨、挥笔书写的慧旭,肯定体会到了一个书写者的快意,也看见了乡邻们对文化人古老的敬意。年根岁末,这幕书写春联的场景,慧旭是不会忘记的。一年又一年,一颗小小的种子落在了他心中,一滴墨水也在他的身体里晕化开来、激荡起来。记得我大学毕业工作后每次回家,见到姐夫、姐姐,我几乎很少听到他们谈慧旭的文化课(1980年代的乡下,孩子们还是散养,没啥升学压力),津津乐道的总是他们儿子字写得好,比高年级的学生好多了。然后,就是托人到城里买字帖。那时,正兴起一股硬笔书法热,慧旭自然也被卷入其中。进入中学后,慧旭也凭着这“一招鲜,吃遍天”,在同学中有了自己的江湖地位。当然,一个农村孩子身上总是承受着整个家庭的期望,他的未来不可能系于“写字”上,懂事的慧旭没让父母太操心,顺利考上了大学。
为了谋生,他毅然选择了建筑工程专业。然而,钢筋水泥并没有能固化一个年轻人梦想的翅膀,从读大学到走上社会为生存奔走,慧旭的一颗心由楷书而行书,时而也会草书,他体会到生存之艰、生活之味,躬身前行之际,书法梦始终伴随着他。而且,这些年生活于历史文化名城苏州,沐浴吴地文化,广结书友,加上多位前辈春风化雨、泽被后生,使他心有所得,书艺渐进。作为见证成长的我,自是欣慰有加。这几年,慧旭成家、生子,为生活忙碌,我与他的交流更多时候是在节假日的返乡之旅。
我们说乡土故旧,谈开卷获益,话吴地文明,而对于书法则很少言及,原因之一是,我只是个看客,偶尔驻足,从中获取片刻审美之娱,即使偶有沉浸,也是从这个“中国文化最纯粹、最玄妙、最有代表性的载体”里汲取一点营养,以喂养我的写作。当然,作为长者,我对慧旭的书法还是有所期待的,因为,我不仅希望他作为一门艺术热爱它,而且可以作为人生之修为、心性之功课,养浩然之气,领悟书道之本质,在广博渊深之书法文化大峡谷里,坐实“学”“问”根底,苦心孤诣,钻仰不尽,紧紧攥住超越之索,寻得豁然开朗之境。当然,我更有一言要赠与志在习书的慧旭。前辈论及文章千古之事,曾有言曰:非人磨墨,磨墨人也。慧旭阅读有限、阅世还浅,苦难这一课还未真正经历,特别是心的磨洗,而这正是书家必修之功课。历览古今前贤,莫不如是。《丧乱帖》包含的雄强、惨淡之美 ,是右军那一刻的真面目,是大书家的真风骨;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看似粗头乱服,不衫不履,但其深厚功力在涂改增删中表现无遗,是“无意于佳乃佳尔”的典范;吴镇晚境,心无挂碍,草书《心经》所达到的荒寒境界;孙过庭备遭坎坷、一生落魄,却写出了雄视百代,日久常新的《书谱序》,“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他发出的金石之声,是书法艺术的妙谛,也是对真书家的呼唤。于是,我借这几个字告诉慧旭,“向下之路,就是向上之路”,你以心为师了,才会懂得“无声之音,无形之象”;你为之付出毕生心血了,或许有可能“囊括万殊,裁成一相”。非常有趣的是,那年那月家乡某位老者竟给我外甥取了一个很书法的名字——张慧旭。殊不知,他竟敢在唐代草圣张旭的名字里嵌进一个“慧”字,这不是自作聪明吗——我无意怪罪那位已故的老者,我只是想对慧旭说,既然你扛着这个来头很大的书法名字,就认这命好好爱书法吧,幸好,你吃的是建筑饭,在盖大楼这一块你肯定比唐代老张旭“强”那么一点儿。这样想来,你也就可以磨墨捉笔“旭素狂草”了。
这篇小小的序文行笔到此,该收尾了吧?我忽然想起宋代词人辛弃疾的那首《清平乐·村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辛弃疾描写的是一幅生活气息浓郁的乡村风俗画,宁静、安定、富有情趣的劳动和生活镜头,让我想起了我与慧旭的故乡。而最让我感到亲切的是,我姐姐家也是三个孩子,慧旭是最小的一个,我一直喜欢亲切地叫他“张三”。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那个溪头卧剥莲蓬的无赖小儿,在我想象中,也许就是张三吧。作为舅舅,我希望他成长,也希望他永远保留一颗单纯、简静之心,作为一个书写者,你要保留内心那种自然、率性、稚拙、质朴的天籁。这片小小的序文,缘于外甥张慧旭与书友的一次书展,由张慧旭联想到张旭,由张旭想到草书。我之逸笔草草,岂敢累及草圣,不过,我还是要偷懒了,将这篇小文名之为《“草”书于前》。我之草草,草率之草,老家狗尾巴草之谓也。
2013-04-30夜,无锡,京杭运河之侧(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无锡日报社文教专刊部主任)
 手机版
手机版 |
书画
|
书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