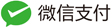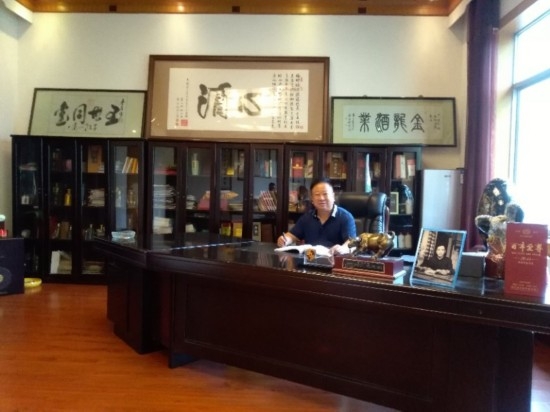记得老楚同志小时候,看的第一部中国电影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第一外国电影是朝鲜电影《卖花故娘》。大概那时候六、七岁,具体情节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很悲惨,就好像看完电影后,还要摸黑深一脚、浅一脚的回家,真不知道该怎么走,能否完整的走回家里。

1991年夏天,陪台湾中华管理学会理事长范光陵博士率领的代表团到上海,在新锦江饭店见到了白杨女士。记得当时范博士介绍《一江春水向东流》远比我这位生活在大陆的青年,感触深刻、感慨迫切。而此时白杨女士却笑容灿烂,如坐春风,完全没有那位殉情于一春江水的臻贞女性,遗恨春江向东流的黯然,唯有阳光,但总是让人觉得若有所失,有点惆怅。
还记得小时候读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总觉得:
春江潮水连海平
海上明月共潮生
滟滟随波千万里
何处春江无月明

----似乎太虚情假意,总不如亡国之君李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那么真切与真实。也不像白居易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借酒消愁愁更愁,让人觉得这样的春江,才更像春江。然而,春江水暖鸭先知之春江,具体应该是那一条江呢?屈大夫沉江之江,抑或西楚霸王自刎之江?我想无论如何,总有一冮春水,洗尽铅华。
酒煮江湖蒸乾坤
梦回汉唐醉昆仑
非谓周郎器量小
遗恨春江不向东

-----此之周郎,三国周郎赤壁之周公瑾也好,周公解梦之周公吐哺之周公也罢。总之,人无遗恨非完人,而遗恨春江不向东,却遗恨的巧妙,遗恨的恰到好处,恰到地方。就是该恨就恨,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要等到关羽大意失荆州的时候。
 手机版
手机版 |
文化
|
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