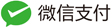李冼洲的文字,是一捧北方的泥土——粗粝中藏着温热,质朴里孕着锋芒。这位作家,其笔端始终带着土地的厚重与人文的赤诚。读他的散文,如饮老茶,初尝平淡,回甘却在喉间久久不散。
《父亲》里,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跨越时代的信物。父亲从“板脸瞪眼”到“抱妹谈书”的转变,让我想起木心所说“所谓父爱,是一种深沉的注视”。他不写“父爱如山”的空泛,只写借书出书的奔走、刮胡扮靓的细节,却让这份爱如暗涌,在字里行间奔涌成河。
《荷花朵朵开》的笔意,颇有周敦颐“出淤泥而不染”的遗风,却又多了几分现代性的温柔。他写荷花“微微的笑如蒙娜丽莎”,让古典的高洁与现代的审美在此共振。正如叶芝所言“万物皆有灵,在凝视中苏醒”,李冼洲的荷花,是自然的精灵,更是人心的镜像。
《蝴蝶飞飞》里,梁祝的化蝶与庄周的梦蝶在文字里翩跹。他写蝴蝶“飞过森林,掠过高原”,让这小小的生命承载了“存在与虚无”的哲思。罗兰·巴特说“写作是一场蝴蝶的迁徙”,李冼洲的蝴蝶,便是这样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学迁徙,从古典飞到现代,从物象飞进灵魂。
《从草原寄出的信》最见其“在地性”的写作态度。那盐碱地的水、老人的窝棚,让我想到加缪笔下的阿尔及利亚荒原——荒凉却充满人性的温度。他不美化草原,也不渲染苦难,只如本雅明所说“在废墟中打捞诗意”,让这片土地的褶皱里,开出真诚的花。
《伤心一个冬天》的青松,是存在主义的隐喻。它的枯萎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正如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叩问。李冼洲写的不是一棵松树的死亡,而是生命在挫折中觉醒的瞬间,这瞬间,便是青春最深刻的注脚。
李冼洲的写作,是一场“在大地上写诗”的实践。他的题材如北方的平原,辽阔无垠;他的情感如地下的泉眼,澄澈甘冽;他的哲思如夜空的星子,遥远却明亮。
他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有“清水出芙蓉”的本真;没有刻意的深刻,却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力量。这便是他的风格——像北方的风,自由、直接,却在吹过之处,留下一片思考的麦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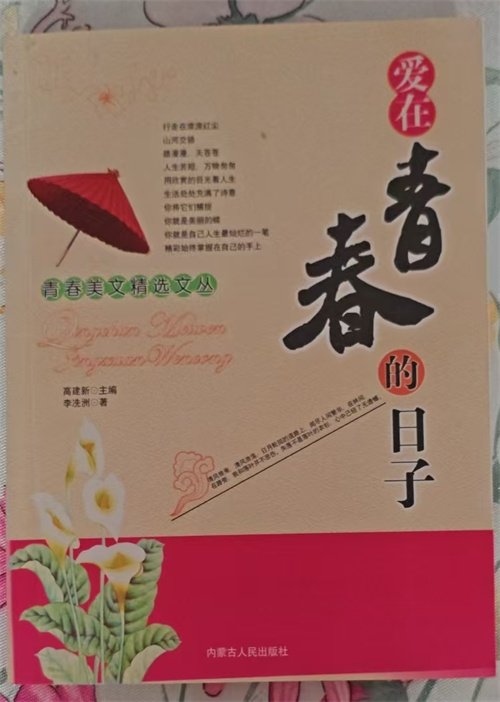
读他的《爱在青春的日子》,便知青春从不是年华,而是一种“永远在路上”的姿态。
近日,他的新诗集《云过三千》又喜文出版,更让这份期待愈发炽热。好期待翻开《云过三千》的扉页,看他以诗为笔,再绘山河辽阔与人心深邃;好期待重逢于他的诗歌朗诵会,再沐文字甘霖,沉醉于这场文化的饕餮盛宴;好期待他以笔为马,在文学天地持续驰骋,用兼具真诚与哲思的作品,继续滋养我们的精神荒原。
 手机版
手机版 |
综合
|
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