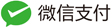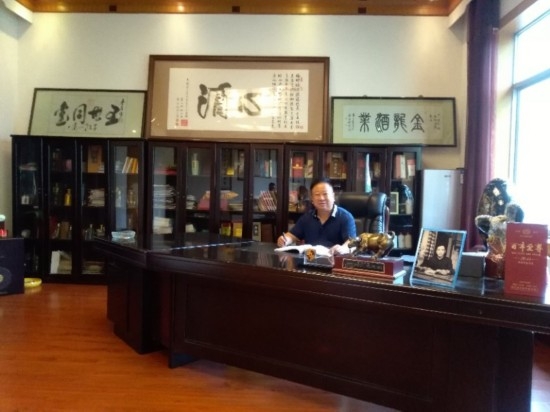酷暑中,一群群白鹅或在水塘里惬意地游弋,或在绿意深深的桃树林下“嘎嘎”地聊着 “鹅”事,人一接近,便“哗”地一下散开来,与人们平常接触到行动缓慢的“笨鹅”完全不同。顾盼行走之间则神态高傲、步伐霸气、叫声圆润,呈现出了一幅生态动人的画面。这是笔者在傅玲娟的养鹅基地看到的场景。
傅玲娟是武义县壶山街道后舍村吉祥寺自然村人,养鹅之前她在一家企业做采购工作,一个月也有五六千元的收入。今年因疫情几个月没上班,也就没了收入。正当她苦闷时,一次与朋友聊天,朋友说20多亩的桃树林里杂草又很多了,雇人工拔的话,每个人工要100多元钱一天的费用,实在在吃不消,自己拔又累。反正现在没工作,叫傅玲娟到桃树林里养鹅算了,因为鹅能把草吃得干干净净。
朋友无意中的一句玩笑话,勾起了傅玲娟小时候家里养鹅的往事。那时候家里每年养有10多只灰鹅,每天一放学,傅玲娟就把鹅往田野赶,顺便拔一些青草回来给鹅当夜宵。灰鹅长大了,父母就拿去卖掉,给她当学费和零用。
通过市场调查,傅玲娟发现现在吃鹅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永康一带,在一些传统节日,鹅往往供不应求。在春节前夕,一只鹅甚至卖到几百元,上千元一只。她还记得一次曾经专门从武义县城驱车到一家专卖鹅肉的小酒店去吃,如果不是电话提早预定,在这家酒店还吃不到,生意很是红火。而在武义,专门养鹅的养殖场几乎没有,一些农户养个几十只、上百只就算多的了。
闻到商机的傅玲娟与丈夫商量后决定到朋友家的桃树林去养鹅。村里的很多年轻人都想着到城里工作,她一个女人家却 “一根筋”似的到农村搞养殖。对于傅玲娟的做法,很多亲朋无法理解。父母也十分纳闷:自己一辈子在农村干农活也就算了,女儿却执意在农村从事养殖,让人想不通。

在一片质疑声中,傅玲娟脱下平时穿的时髦服装,换上了干农活的衣服,戴上草帽,扛起锄头,在桃树林里平整土地。为了节约资金,大多数的活都是她和丈夫自己干,自己铺路、砌鹅舍。足足干了半个来月,一个养殖场终于初具雏形,养鹅创业也终于迈出了第一步。
4月中旬,傅玲娟从江苏以每只35元的价格购买了1000多只鹅苗,毛茸茸的,很可爱。从那时起,她就当起了全职的“鹅妈妈”,白天喂它们吃东西,晚上看着它们睡觉。“小东西喜欢挨着身子压着睡觉,要是不把它们分开,小鹅容易被压死。”傅玲娟回忆起当初照顾鹅苗的经历。
为了养好这些鹅,傅玲娟买来专业养殖书籍,并从网上查阅相关技术资料学习,结合农村传统的土方法进行养殖。在荒郊野外,傅玲娟用对未来的美好憧憬驱走寂寞和孤单。
食料以吃玉米和草为主食,水源都是水库的活水,鹅在水塘里自行吃小鱼、螺蛳等水生物,起到了调胃口的作用。鹅从幼苗都是放养,满山跑,满水游,鹅的体质特别好,行动敏捷,想抓只鹅要费好大劲。

经过3个月的艰辛付出,养殖获得了成功,当初那群毛茸茸的小鹅,变成了漂亮的“白天鹅”。一般家养的成鹅,基本能达到5公斤以上,而她在整片桃林中养的鹅大部分都是3到4公斤,鹅肉比一般家养的鹅味道更为鲜美。8月初开始上市销售,短短几天时间以每斤17元的价格销售掉了200多只,基本都是通过朋友圈在亲朋之间销售。也达到了朋友当初开玩笑用鹅除草的目的,而鹅粪可以当果园肥料,循环利用资源。
傅玲娟说,由于没有经验,一下子养了1000多只,在同一时期长成成鹅,不可能很快就能卖掉,就增加了成本,每天要吃掉约
200多公斤的玉米。以后,她将每隔个把月购买回两三百只鹅苗,以递进的方式进行养殖和销售,以降低成本和风险,促进养殖业的良性发展。她相信,自己一定能通过养鹅走上小康之路,对此她很有信心。
拔鹅毛比拔鸡毛难一些,有些人就因为这个而放弃了这一美食。傅玲娟介绍一个巧门,在烫温水里加点盐,有助于拔毛,也可以每只鹅加20元的加工费,通过她请人人工拔鹅毛。(王东方)
 手机版
手机版 |
基层
|
基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