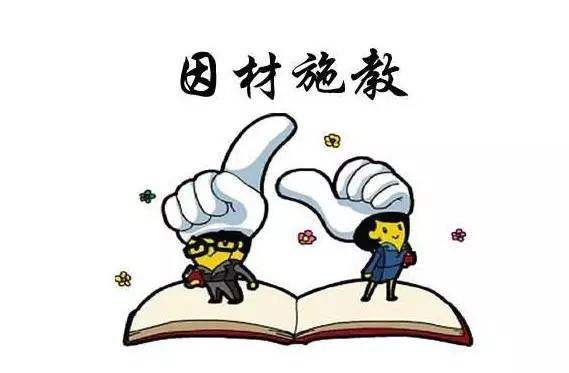
自从三年多前开始写公众号,每年教师节都要写一点东西,今年也不例外,谨以此文纪念2019年的教师节。
几天前,在学校食堂吃晚饭,遇到一个在初一国学课上曾经教过的学生,现在上初三了。他看到我很热情地打招呼,打过饭之后,我们坐在一起,边吃边聊。
“我听下一届有学生说水寒老师的课索然无味,令人昏昏欲睡,可是,为什么我却感觉不一样呢,尤其是到初三了回想起来,更觉得您的课值得细琢磨,越琢磨越有味道。”
他的话引发了我的思考。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哪一个是真的呢?从我个人意愿上来说,当然希望后一个是真的。但实际上,前一个也应该是真的,因为确实有一部分学生在我的课上完全不在状态,神游八荒。
难道是我的课讲得越来越差了吗?应该不会,因为连续三年都在教初一的国学课,有一些课经过反复打磨,肯定比第一次讲得更深入,更生动,更细致。但为什么却越来越不受一些学生的欢迎了呢?
难道是我对上课的热情减退了吗?随着教师生涯年限的延长,确实难免有一些职业倦怠感,但我仍然时时提醒自己,要对得起自己教师这个名号,要对得起每一个学生,所以尽可能用心去准备每一节课。但为什么这用心准备的每一节课,却有学生完全游离在课堂之外呢?
难道是因为我所讲的内容没有价值吗?虽然有人说“国学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但是我在设计国学课校本课程时,尽可能在涵盖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和现在的中高考紧密地结合起来,争取让学生不仅能够感受到这个课对于人生的“大用”,也能体会到对于考试的“实用”,但为什么会有学生完全无法体会老师的良苦用心呢?
难道是因为我所讲的人生道理太多太艰深了吗?我愿意在我的课堂上,尽可能引经据典地谈对人生对时事的一些认识,发表一些看法,让经典观照现实,让经典活起来。而且有相当一部分课例在我写成公众号文章记录下来之后,引发很多人的共鸣。难道学生不觉得这些会对他们有用吗?
……
有多少个难道,就有多少个问号。但这个问号背后不是不被理解的委屈,而是由此引发的深深的思考。
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我想起亲历的两件事来,或许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其中。
一件事发生在刚刚开始走上教师岗位,当小学老师不久。
一天,我在给学生讲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一边讲解,一边让学生表演一下诗歌中描述的情形,大多数学生除了觉得“笑问客从何处来”这个情节有一点儿好笑之外,还能体会到诗人本来是主人却被当成客人的无奈与心酸。
在讲完这一首之后,就很自然地顺带扩展了《回乡偶书》的另外一首,“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当我讲到“离别家乡岁月多”就是换了一种说法的“少小离家老大回”时,学生频频点头。我把“近来人事半消磨”和“乡音无改鬓毛衰”两句联系在一起,启发学生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诗人已经衰老,但却功业未建,颇多感慨时,也有学生在点头称是。
但讲着讲着,我自己就不太关注学生的反应,而完全沉浸在诗意之中了。自言自语地感叹“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这两句诗写得实在是太好了,不动声色却直指人心。人与自然相比,人是多么渺小,与自然相比,人生是多么短暂啊!这样想来,人生充满了一种无常感,一种强烈的悲剧感。
一番慨叹之后,忽然发现全班静悄悄的,我以为他们也因此而感动呢。抬起头来看学生,发现他们都直愣愣地看着我,原来他们不是感动,而是疑惑,他们完全不能理解老师所讲的什么人生的无常啊,人生的悲剧啊一类的东西。也难怪,他们只是五年级的小孩子,怎么可能对人生的无常和悲剧有体会呢。
看到这样的情形,我不禁哑然失笑。我只感动了我自己,但却无法感动学生,不是因为我讲的不好,不是我讲的东西没有价值,而是因为他们的水平还没有到,他们的年龄和阅历还没有到,他们还很难理解我所讲的这些内容。
另外一件事则发生在我读大学期间。
刚上大学,见识到各种各样的先生,和初中高中的老师不同,不再强调什么这个是考点,那个很重要之类,完全放开来挥洒自如地讲。用现在的话来说,那时候就有很多老师成为学生心目中的“男神”或“女神”。
那时候喜欢什么样的老师呢?喜欢那些在课堂上会讲段子的老师,在轻松愉悦中听听《诗经》《楚辞》,听听唐诗元曲,考试随便写一点东西就能过。而不喜欢甚至有一点儿怕什么样的老师呢?怕的是一张口就引经据典说什么《碧鸡漫志》(注:一部记述、评论和考证唐宋歌词和乐曲源流的重要文献)中怎么说的老师,怕的是一考试就要考各种细节,看你是否真正读过原著的老师。
但大学毕业过了若干年,读的书多了,经历得多了,同学聚在一起,再谈论起来时,忽然有一些一致的意见,原来当年那不断引述《碧鸡漫志》的老师,才是真正做学问的老师,才是真正高水平的老师,而那些讲段子的老师,则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已。
以上两件事本质上并无不同,我没有五十步笑百步的资本,我和我的学生一样,我也因为年龄阅历的因素,无法能够在当时对老师所讲内容的价值做出准确判断。
那么,接着的问题就来了。
作为老师,我们该给学生讲什么,怎么讲呢?虽然有诸多有关教育与心理的最新研究最新理论,但实际上,说到根底还是一个教育中的老问题,那就是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是教育中的理想状态,但现实中,要想做到因材施教,却存在种种障碍。
比如,在班级制授课的状态下,又因为教育部门不允许根据学生水平分班,所以学生的水平差异就很大,两极分化就很严重,那在教学中,更应该向哪一部分学生倾斜呢?是最顶尖的,还是最末尾的,亦或是中间的?可能大多数老师都会选择多照顾中间学生的办法,但如果班级学生水平呈橄榄型分布还好,如果不是橄榄型,而是哑铃型,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又比如,老师和学生接触的时间问题。前些年我教语文课,虽然也遇到过所讲内容因为学生水平有限,不大能接受的问题。但因为几乎每天都有给学生上课,与学生相处的机会,在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中,学生的这种不适感就慢慢消失了,水平就慢慢提升上来了。但在改教国学课后,每个班每周只有一节课,课时少,意味着能够对学生发生的影响就小,潜移默化的可能性就相应变小,由此是不是要根据老师与学生接触的时间长短,对教学的内容与难度做出一些调整呢?
再比如,随着社会上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氛围的加剧,相当一部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变得更为急功近利。他们认为考的就有用,不考的就没有用,考的就学,不考的就不学。但如何给学生讲清楚,有些东西不是今天考了,对明天就一定有用,反之,有些东西今天虽然不考,但却是明天的必须呢?
还有,很多学校会组织学生对老师进行评教,从教育教学等不同维度进行用户满意度调查。这当然有助于促进教师改进教育教学,但也会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老师的一种无形的压力。是要所有的学生都满意才是好老师吗?如果不是要求所有的学生都满意,那多大比例的满意,可以认为是合格乃至优秀呢?如何平衡优秀学生和学困生的不同教学需求之间的矛盾呢?如何平衡学生的现实认识水平和将来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呢?
……
以上很多问号,在现阶段,有的有解,有的无解,更多的是难解。但思考与不思考毕竟有着本质的不同。我只想说,教育是一个且思且行,且行且思的过程,对于教师而言,因材施教,永远在路上。
